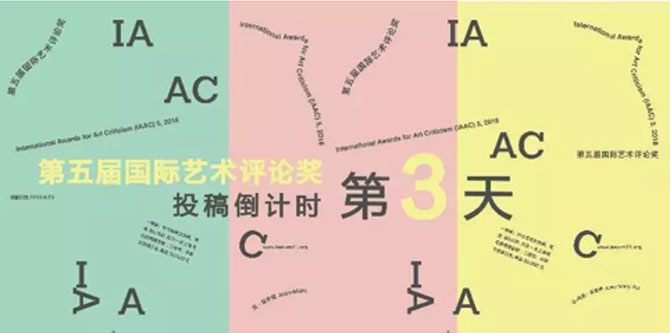
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在每年征稿期间,都会推出与艺术批评相关的系列访谈文章,以飨读者。本期介绍IAAC组委会成员凌敏女士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的访谈。詹姆斯是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与批评系主任、爱尔兰科克大学美术史系主任,著有《绘画与眼泪》《图像的领域》《视觉研究:一种怀疑性的导论》《艺术是教不出来的》以及《视觉品味——如何用你的眼睛》等。
凌敏(以下简称 L):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开办至今年已是第五届。设立此奖旨在推动艺术评论,鼓励并发掘中国艺评人。IAAC有一套评审流程和国际化的评审团。从过往的情况看,大部分获奖者是艺术家、策展人或其他艺术从业者。
詹姆斯•埃尔金斯(以下简称 J):IAAC能影响到年轻一代是很重要的。
L:趁你在上海,我想跟你讨论几个问题。首先问一下美国的当代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是否服务于大众?而目前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市场主导的意味比较突出。有些作品(包括绘画)并不能被划入当代艺术的范畴。就你来看,艺术评论家在这中间可以做些什么?充当什么角色?
J:我想你的意思是,要想使观众更多地参与到当代艺术中,艺术评论家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我的回应也许会出乎你的预料。
你也知道,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艺术评论会议有很多,会上大家总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前些年我同时受邀到不同国家于同一天举办的两场会议,一场在哥本哈根,另一场在加拿大。当时有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是艺术评论家做的事情应该与众不同。但我曾问过《纽约时报》艺评专栏作者迈克尔•基姆尔曼(Michael Kimmelman),想了解观众是否会对他的评论有很多负面反馈。他答复我说:“坦白讲,如果你读过我曾收到的一些读者来信,绝对会大吃一惊。”
在他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是在获取他们想要的,如果报纸减少了批评写作的篇幅和数量,那写的人就越来越少,读者也会越来越少。批评不是去改变想法,而是让读者试图理解,我的题外之言到此为止吧。因为现在我所听到的呼声,几乎都是在说艺术批评要变得更专业、优雅、高效等等,但事随境迁,大家都忽略了理解与接受当下的现实发展也很有必要。观众想从电影、戏剧亦或是舞蹈、音乐等各类艺术作品中看到什么样的评论,他们或多或少地已经从各种媒体上接触到了。 据我所知,没有人是为了评论而评论的。通常大家认为评论人的责任在于为社会实践带来改变,例如帮助改进教育质量。换言之,这是个社会问题,也是公共政策的问题。主流的报纸总是与权利相关,语境严肃。艺术评论家应该将新的突破口转移到网络上,目前网络社交媒体大热,出现了许多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杂志、博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
L:目前,中国有很多平台涌现出来,尤其是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等。但年轻艺评人仍觉得路很窄,想要在主流的艺术报刊杂志上发声比较困难。而现实是各种展览和艺术活动又特别多,大量信息迅速更替,但真正扎实有份量的评论声音少之又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J:对于一件事,直言喜欢或讨厌比解释更有意思。以艺术评论的指示功能仅对部分(而非全部)受众受用。网络上有很多针对某件商品的评论,例如亚马逊(Amazon.com),那些只是买家纯粹的个人判断;而学术评论家绝不会以此类材料为据,那完全算不上批评。
批评绝不是单纯的喜好表达,而应当是一个自我内在作用。一位批评家说,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反复不断地追问与质疑,某一个时刻心领神会就促成了批评。如果不能有内省、反思的作用,简单的判断无法指引读者。艺术批评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批评”,我们要表述的内容另有考量。
L:但有时候对批评家来说,说真话真的不容易。另外,有些画廊、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付给评论者报酬,你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都在掌控之中。
J: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现在还留有在芝加哥写的一篇“打破规则”的评论文章,当时我应一家画廊之邀写一篇“正确”的稿子,完稿后画廊那边却说你的稿子里有一些批判的成分,不能作数,于是稿子就被“枪毙”了。由于对方已向我支付了稿费,所以我也不得在其他地方发表这篇稿子。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有一个在爱尔兰举国皆知的评论家,长期给当地报纸供稿,名字我就不透露了。他这个人非常好,几乎从来不写带有负面批判色彩的文章。有一次会议他记错了时间,当即决定不出席了,一来是不想被看到,二来不想点评任何人。所以他能做这个工作就太奇怪了,他在一个局限的枷锁里书写事实,我就很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错的,以及他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是个人,必定有自己的考量,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呆在一个圈子太小的地方。
L: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比较火,一些美术馆、画廊在力捧各自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迅速,但艺术理论和评论却没有同步跟上,你对此怎么看?
J:我对中国艺术批评所知甚少。我认识一些中国理论家和艺术理论的中译者,我知道很多人在研究这一领域。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及评论领域存在着三个问题。
首先,很多西方的艺术理论翻译成中文之后历时久远,渐渐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脱节。
其次,大部分英文理论是从法文翻译来的,其中又以法国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理论最为批评家所钟爱。几乎在我知道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法国后结构主义的身影在解释一些艺术现象,而不管事物的本身是什么样的。上述第二个问题是一直被忽略的——即使是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艺术理论的中国,为什么法国后结构主义就足以取代其它理论呢?它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频繁地使用。
第三个问题是理论的命名存有不公平性,许多艺评人可以轻易说出一大堆西方(尤其是法国)的艺术理论,却对中国的艺术理论知之甚少。因此,关键在于必须改变大众的习惯。
L:你的观点是,艺术批评、艺术理论或许不是那么全球化。
J:是的,可以这么说。
L:在中国本土,我们还没有看到系统的、一脉相承的艺术理论已经出现,这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
J:中国的传统艺术理论基本上均源于古典绘画,一些文本自唐朝流传下来。这本就无可厚非,但现在却被当作是中国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艺术理论。同时,虽然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仍然可以用于当代艺术领域,却也存在潜在风险,因为无法摆脱这种局限。
L:的确是这样,从明、清流传下来许多绘画理论,但要转译成英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见过一本理论书,讲的是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传统艺术所代表的过去是当代艺术之父。事实是,在不同阶段,无论是相仿抑或相异,艺术总会呈现出多姿多彩、互为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面向。你觉得最有趣的艺术评论议题是什么?
J:我总是在想,对于一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的评论,会存在哪几种评判视角,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毕竟,没有争议就没有改变。但要弄清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视角。我的意思是,评论结果往往是跟着评论者所选择的角度走的。评论家能看出很多问题,不同的写作方式对应不同的评论角度,在决定评论角度之前要先确定写作的方式。
L:照你这么说,评论不再具有普适性了。
J:我不确定我的理解是否像你说的那样,但是评判视角一定不是全球性的。
L:因为你说艺术评论不是全球性的,所以我这个判断是从你的观点推论而来的。
J:我的意思不完全是这样。当我说批评不是全球性的,是说大家有不同的艺术评论风格。现在艺术界变得非常单一,人们在这其中互相竞争,而我们的艺术评论风格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对于一个背景薄弱的年轻人,他可能会选择现成的理论套用到周遭的艺术家身上。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惜了,因为他缺乏艺术一直所追求的东西,那就是创新理论。
L:你对自己的定位是评论家、历史学家,还是理论家?在你心中排第一位的是哪个?
J:有人说我是艺术史论家,我觉得挺对的。我研究的是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之间的对话是如何发生的,这不需要评判,把所有事实罗列出来后更易于比较。
L:能介绍一下美国艺术批评的现状吗?我们曾有一个二等奖获得者是美国人,她提到当前美国的评论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尊敬,而是变得越来越难以生存了。
J: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间,我没有看到美国艺术评论有什么明显的巨大变化,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变化。美国艺术评论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由市场驱动的,由于假设越来越多读者对艺术评论缺乏兴趣和关注,导致主流媒体和出版社对艺术评论文章及著作的篇幅及数量每年都在削减,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比德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地严重得多。
L: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译者:刘艺、子叶
本届国际艺术评论奖奖项设置
一等奖:
中文或英文作品获奖者一名,
奖项得主将获得奖金80,000元人民币(税前)
及一次上海或伦敦的短期驻留
二等奖:
中文或英文作品获奖者共三名,
分别获得奖金30,000元人民币(税前)

高名潞,批评家、策展人,匹兹堡大学教授

沈语冰,复旦大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特聘教授,兼浙江大学世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萨莎·克拉多克,作家、评论家、策展人,布隆伯格新当代艺术(New Contemporaries)委员会主席

让-马克·普安索,艺术批评文献库创始人兼主席,《艺术批评》杂志编辑,雷恩第二大学名誉教授

马修·科林斯,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作家及BBC电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