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国际艺术评论奖开幕式前夕,往届获奖者和入围者们从世界各地赶来,齐聚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这是IAAC大家庭第一次大团聚。在短暂的下午,十三位青年评论人从自己写作的心路历程出发,就“批评的立场”各抒己见。
讨论主题: 当面对一个具体的展览或者现象的时候, 怎样在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批评的立场?

苏伟:“能不能在感同身受和抽离之间找到很动态的平衡,这是一个挑战。”
做研究对一个批评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训练,事实错误和基本的立场错误不能犯。一方面要感同身受,回到艺术家创作现场,回到发声的语境里,关注他的生长过程;另一方面从中抽离,把它放到更具体、更有机的环境里去看。一件事有多个连接点、多个指向,反问自己如何从同质性中找不同,从图片中找到诉说的真源,从各种创作里发现一些真实的轨迹。

金雪岑:“其实我们可以以各种不同身份介入艺术写作。”
通过艺术评论奖,我有幸结识了同在巴黎朋友,我们一起创建公号,一起写作,他们有的是艺术家,也有学哲学、学艺术史的,我们身份不同,从不同视角切入同一个展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陈涵:“对于上世纪艺术评论的回顾和反思或许更有利于当下的艺术评论家和研究者在当今的文化语境里去完善我们批评语汇。”
我是现场唯一一个在读研究生,我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我对艺术评论的接触和理解,都来源于我的艺术史学习研究经验,我想以我自身的经历谈一下我对艺术批评的了解。
艺术评论立场架构首先应该和批评者的学术背景、脉络相吻合,这一点在西方现代艺术评论中非常明显。以展览评论为例,展览现场交互性体验固然会给写作者带来了灵感,但是仅仅依靠这种现场感和历史途径概念的写作,难免会显得有一些单薄。所以展览评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转述现场,还应该为读者提供高于艺术表现形式的思考空间。另一点是在强调学术性的基础上,我个人认为艺术评论也应该保留一种可读性, 考验当代批评家如何为普罗大众构建一种源于批评术语又高于批评术语的新视角。

张未:“互联网出现,我不觉得这是个危机,我觉得是个转机。”
在今天的互联网社会,人们自我觉醒了,认识到自己有这个能力,于是我们要批评,我们要言说,我们忍不住想要对他进行批评。我想说,可不可以从自我觉醒变成自我决定。我们作为批评者的时候,深入到了艺术之中,借由技术、AI这些成为艺术创造者的时候,我们开始应该从觉醒变成决定,我们可以给出意见。网络评论,本身也有他的价值,但这个价值的可能性在于批评的深入程度。

周昕:“如果一个评论人拒绝进入艺术家所设的条条框框,那么怎么办?”
我是学习电影学的,没有受过正统的艺术史训练,开始是写一些纪录片评论,然后到影像、纪录片的展览,后来慢慢到博物馆,我的一些文章也刊登在艺术类出版物上。我想说的一点是,比较偏研究性的艺术家,他有自己的理论或者是成文的文献,作为观看者一则没有那个时间,又或是我不想进入你所给的那些条条框框,只是想要从视觉或者展览本身去获得感受,这类的评论文本很容易变成类似大字报的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

李思思:“最有价值的就是主观的这部分。”
艺术评论最重要的还是从独立的角度出发,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客观的描述作品。二是从主观出发阐述和评价。艺术家和作品之间,也许艺术家自己创作了作品,但是这个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之后,它其实是独立的东西,是艺术家头脑想法的一部分,但这只是他作品一部分含义。一个作品是这个艺术家所经历的一切,不仅是他当时的想法,是他一路生活经历所见所闻,跟他所生活这个时代大背景相关。

杨诗涵:“艺术批评是艺评家的再创作。”
我早期也是写影评,后来才开始写艺术评论。这几年很多学者会谈到“真实”,其实艺术评论也这样的。如果基于学术、事实为基础去写一种散文式的批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艺术评论另外一条道路,因为太过学术的文章会让观众和艺术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艺术评论家可以以一种更有趣的、散文式方式写作的话,可能会拉近观众与艺术家和作品的距离。

陈玺安:“其实今天更有趣的写作是思辨。”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批评,一种是思辨。批评是看一个作者站在哪一个立场,通常批评最标准的格式就是论文,思辨的角度有一个很好的批评性视角,主体不一定要站在具体的框架内,不一定跟这个东西保持距离,批判性地去辩证思考到底有几种思辨的可能。

陈嘉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是实践性互为作用的。”
关于艺术批评其实我想到的是60年代丹托的《艺术的终结》那本书,单线性的艺术史或者是建构性的艺术史论述,已经没有办法从视觉上或者从美学的角度去区分商品和作品之间的差别。但是传统艺术史的线路虽然断了,艺术批评和艺术作品互相互补才真正开始。他认为艺术批评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有补充、启发作用。

王易:“精妙的描述不能代替微妙的判断。”
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断裂感,展览做的越多,我越不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理智告诉我这个是悖论,后来停止工作也证伪了这一点。由这个体会所引起的思考,艺术的魅力和抽象思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样一种张力却一直是我写作的起点,是我在意的一个问题。无论展览或者是事件的评论,对象永远都是经验和现象层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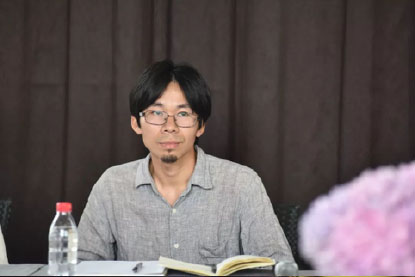
刘加强:“不谈批评的话,我们可以谈判断。”
作为补充提一点关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写作,它可能不是外向批评式的,而是构成其整体工作的一部分。从个人来看,不管是评论写作,还是各种媒体艺术实践,都包含非常多判断,人们在接触作品时也是在做各种判断。所谓的审美判断,或许不一定能完全通过文字表达,怎样让难以通约的审美判断从感受出发,向某一具体语境开放,不见得是必须写成长篇大论的文字,有时候日常跟朋友的交谈或者发朋友圈,也构成了触发互动的微型批评语境。

康晓溪:“其实艺术家在我心中并没有上过神坛,他/她一直是我身边那种缺颗牙的普通人。”
我看一个作品的角度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在实际创作的人,我无法避免地能够体会到创作者本人在创作当中的感受。大家在崇拜、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可能并没有真正在欣赏它的美,我是在感受他的感受,所以才写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前大家都说了艺术不可言说的一个部分,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可言说的,其实很多时候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在自我揭伤疤,过程愉悦并痛苦。我也非常呼吁艺术家能够多多去写作一些他自己创作时候的感受,解剖自己。